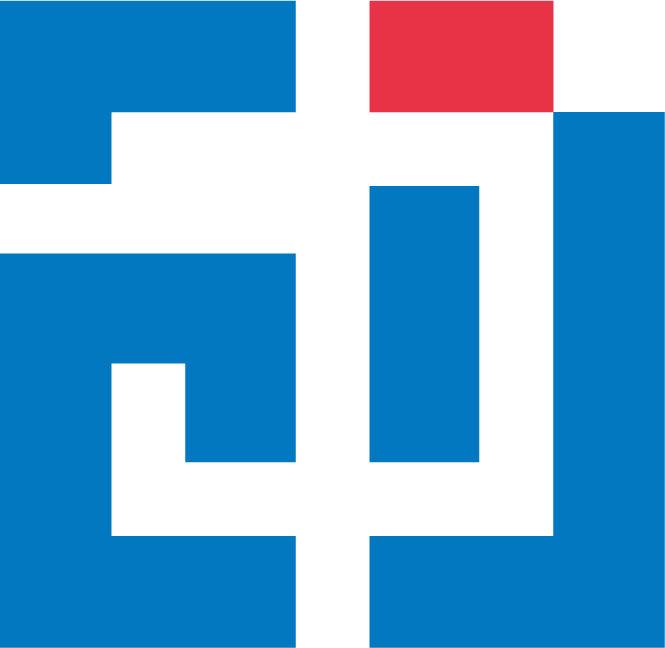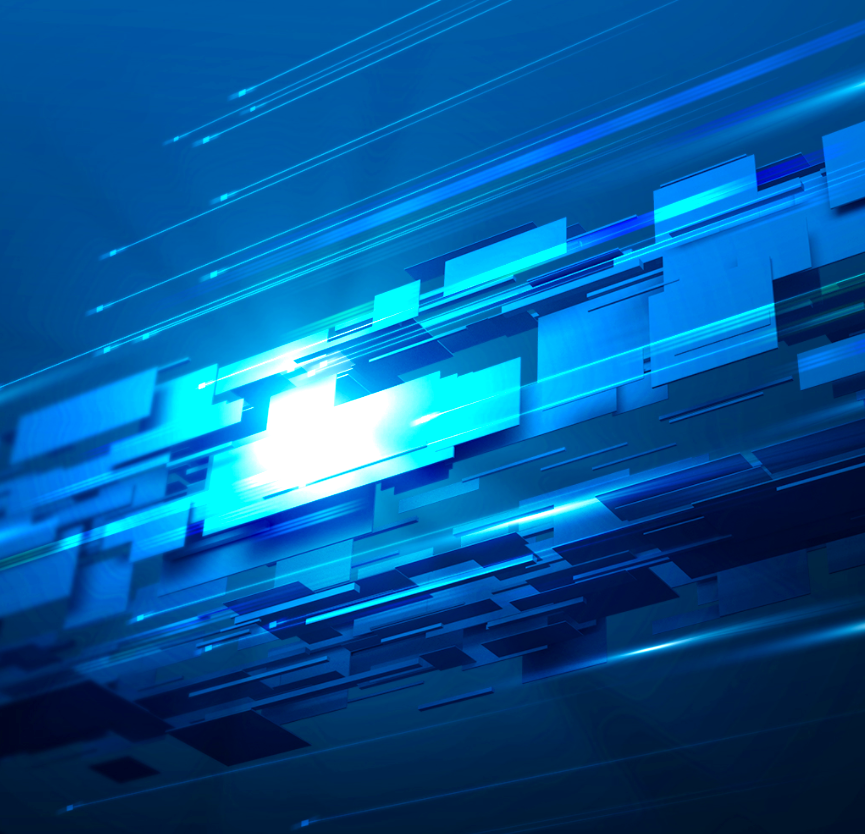区域经济改革系列①: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内涵解析

原创:浦亦稚,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首图:网络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首次在国家文件中正式明确将“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任务。之后国内也掀起了有关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的理论研究,但事实上,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实践探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随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到纵深推进阶段,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成为区域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本质是探索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最佳耦合点”,通过适度打破行政区划障碍,推动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资源更加有效地整合和配置。但在实践中,由于行政区与经济区无法完全兼容,依旧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分离程度”如何在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首先需要探究清楚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内涵。近年来,国内关于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理论研究日益活跃,虽然国际上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但中国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多年的实践探索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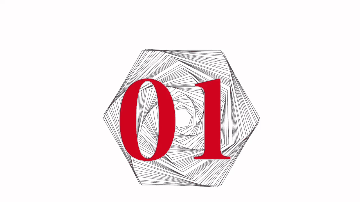

理论源起
1、关于经济区、行政区、经济行政区、行政区经济。经济区指的是经济活动相对独立、内部经济联系紧密、体系较为完整、具有特定功能的地域空间。行政区则是根据国家分级管理需要、人为划分的地域空间。经济行政区指的是在地域范围上与行政区范围相吻合的经济区,兼有经济区和行政区的双重特点和管理职能。行政区经济指的是由于行政区划对于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现象。
2.关于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地理空间关系。国外的经验显示,在市场机制完善的条件下,经济区大多是按照经济联系自发形成的地域单元。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路径来看,设立各类经济区并逐步在点上形成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增长圈层更多是国家战略决策层面的主动作为,既包括综合类的经济区,也包括专业类的经济区,在地理范围上可能小于行政区划,可能等于行政区划(即经济行政区),也可能横跨多个行政区划,还有可能在地理空间上虽然与行政区分割、确与其有着紧密的经济关联(飞地园区)。同时经济区与行政区在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换。
3. 关于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源于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边持续集聚、一边推动协调发展的阶段,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制成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基础,这就要求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突破行政区范围,生产要素可以穿越行政边界,实现跨区域的流动与相互协作。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就是要通过制度的安排,充分发挥经济区的增长极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经济区地理范围以外且不发达地区的扩散,从而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但在现实层面,各行政区处于保护本地市场的需要,会对商品与要素流动施加行政壁垒和限制,具体表现为各行政区产业同构、功能重叠,市场封闭、竞争同质、基础设施衔接不畅等,从而导致“行政区经济”,影响增长极效应的扩散效果。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就是指在不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前提下,通过制度安排对二者的管理权限的进行“适度”划分,将冲突和矛盾限制在最小范围,尽可能让各类要素实现自由有序的流动,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共赢。
国际上来看,主要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互通互联、制定相关政策等方式来促进生产要素实现跨地区自由流动,也有一些城市群成立专门设立的协调机构,集中行使各个区域部分的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经济发展功能,如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双城大都市区议会”、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大都市政府”,以及“华盛顿大城市区委员会”,英国的“大伦敦议会”,法国的“市(镇)联合体”,日本的“首都圈整备委员会”等,协调内容主要包括区域规划,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供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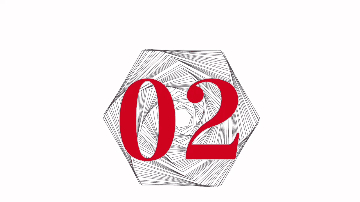

相关实践与研究
有关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理论研究要远远晚于其实践探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区域一体化早期探索建立“上海经济区”的过程中,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就提出“经济中心不必分疆划界,可以相互交错,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组织起来”,这个说法可以看作是经济区与行政区可以“适当分离”在国内的理论雏形。40年来,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朝纵深推进,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实践探索始终步履不停,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支持成渝地区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同年7月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进一步明确,在成德眉资同城化区域、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川渝合作示范区等开展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试点。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首次在国家文件中正式明确将 “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任务。
之后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文献逐步增多,如蔡之兵等认为“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本质就是要避免行政区域的个体性对经济区域整体性的分割。”黄伟等认为“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本质是区域发展权与发展收益权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匹配的过程”。柳青认为“所谓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既要体现‘分’, 行政区要让渡部分经济管理权限,赋予经济区更多的市场自主权;又要体现‘合’,经济区要在保持行政区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腹地的经济联动和有机融合。”盛毅等认为,“在既有行政区划中,设立专门经济功能区或者利用经济关联度较高的特定区域,来履行行政区不适合承担的发展任务与行政区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如何将这些冲突和矛盾限制在最小范围,这就需要研究两者管理权限的适度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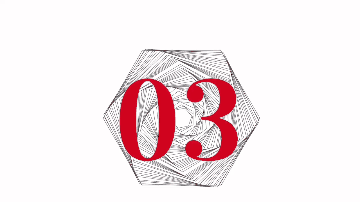

内涵和影响因素分析
1、内涵。所谓“分”,简单地说,就是指经济区与行政区在管理框架上的重合程度,如果高度重合,界定为分离度低或者较低;如果管理边界明晰,切割清楚,界定为分离度高或者较高。以结果为导向,可以对“适度分离”从两个维度界定:一是经济区与行政区之间的制度平滑程度,二是对经济区的发展带动程度。经济区和行政区之间的制度差异划定了各自权力和利益的界线,进而会影响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如果制度摩擦较小,对经济带动程度较高,则界定为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主要表现为要素保障高效率、监管审批强闭环、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较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互联互通水平较高等。因此无论分离度较高或者较低,只要能满足于上述两个维度,都可以称之为不断接近“适度分离”。在低度分离的情况下,一般制度平滑度较高或者不存在制度摩擦,但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程度可能较弱或者不明显;在高度分离的情况下,受发展目标差异、利益主体多元等复杂因素影响,制度摩擦较大或者较明显,但有可能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程度相对较高。
一是地理距离。从地理层面来说,跨地域幅度越大的合作,特别是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的地区,合作趋势大于竞争趋势,合作时制度摩擦也相对越小。地理上更加接近的两个区域,尤其如果两个区域在市域层面,那么在所属的统一行政辖区面临更大经济发展压力或期待要求时,竞争趋势大于合作意愿。实践证明,跨省或者省域之间一体化合作较为成功,而市域层面的合作则制度摩擦较高。
二是发展差距。跨区域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改革在实践层面往往体现为“飞地合作”,如果合作两地在发展水平、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距,两地的合作动力越大,就会形成两地之间合作大于竞争的格局,不仅飞出地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对飞入地的发展带动效应也越强。具体来看,在经济水位差别较大的格局下,为了快速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较低水平区域建立的经济区(合作飞地)基本都会选择行政区级别较高(飞出地)的发展权限和政策,从而拉近两地制度距离,使得经济区的行政管理框架不受到本来所属行政区管理体制的束缚,而是与飞出地行政区管理框架基本重合,尽可能地减少制度摩擦。此类型的合作双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各自的利益驱动不同,可谓各取所需。在这种典型的经济区与行政区相对低度分离的合作模式下,经济区的发展成效较为快速明显,我们可以界定为这种分离的程度是“适度”的。
三是协调层级。从结果上看,合作项目是否具备较高层级的战略定位对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改革的成效、即分离是否“适度”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项目协调的行政层级越高,随之配套的协调机制也就越高效,冲破区划间“行政阻力”的力量也就越大,通常省级或者国家级层面的合作项目,外部的政策支撑力度较大,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制度突破上给予改革试点,有利于提升 “利益引力”,并平滑制度摩擦,从而提高合作效率与质量。
参考文献:
1. “制度距离”对区域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及其治理应对 —— 来自全球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与启【J】,张京祥、王雨,国际城市规划 ,2023(5),56-65
2.尺度重构理论视角下经济区与 行政区适度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 * ——基于 20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谢来位、常阳,中国行政管理,2023 (12),61-72
3.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历史阶段、内在本质与政策建议, 【J】, 黄伟 蔡之兵,中国国情国力,2023(1),65-68
4.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视角下 武汉都市圈的协同治理,柳青,2022(12),54-58
5.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早期实践: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经济区概念的提出与演变过程探析, 林盼【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5),142-154
6.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院 实践逻辑尧典型模式与取向选择【J】, 蔡之兵、 张可,改革,2021(11),30-41
7. 创新要素的跨域重组:机制、 困境与路径创新【J】,胡航军、张京祥,城市规划学刊,2024(1),74-81
8.论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的管理模式【J】,盛 毅、杜雪锋,开放导报,2020(5),28-33

- E N D -
作者:浦亦稚
编辑:龙彦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