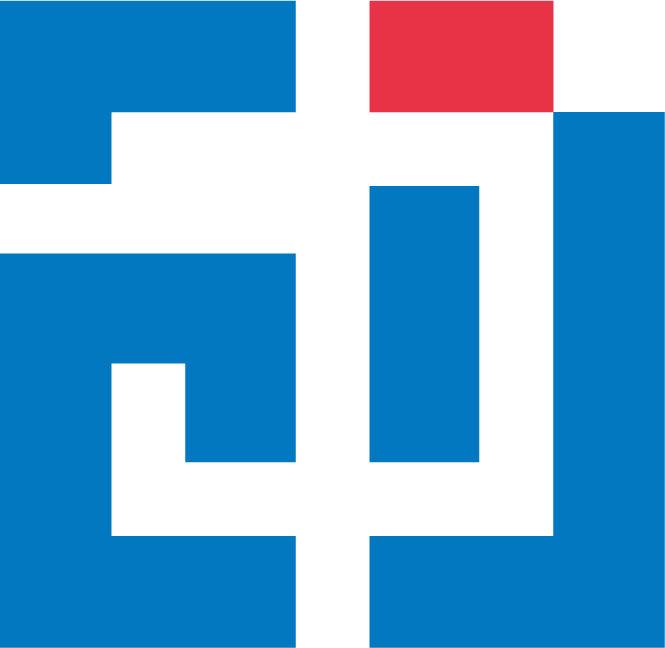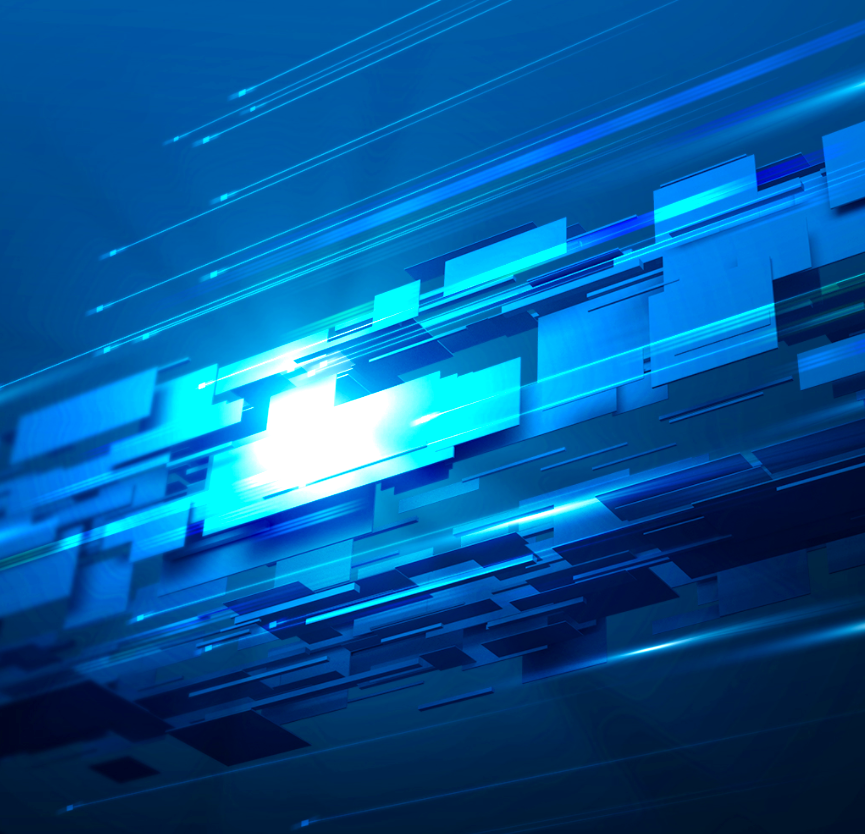区域经济改革系列②: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历程与特点

原创:浦亦稚,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首图:觅知网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改革探索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更迭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路径是先集聚,再逐步走向平衡。当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一边持续集聚、一边推动发展平衡的阶段,就需要打破行政区边界,让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强化区域之间在各个方向和价值链上的经济联系。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改革伴随中国经济从集聚逐渐走向平衡,大致经历了高度分离、高度分离和低度分离并重、适度分离探索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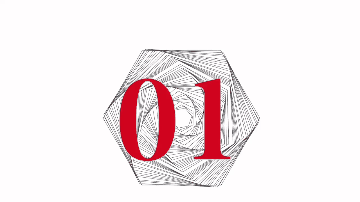

高度分离(上世纪70年代末-2000年):
经济集聚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经济特区、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拉开了中国经济集聚发展的序幕,通过这些经济区在点上形成经济增长极,再由点及带、及块、最后到面,由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在这一阶段,设立经济区就可以率先解决原先行政区内审批手续繁杂、机构叠床架屋等制约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问题,因此经济区与行政区关系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地理边界明晰、管理架构高度分离。
1.经济特区。诞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截至80年代末,中国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大经济特区。成立初期,这五大经济特区的地理覆盖范围均小于全市的行政区范围,通过明晰的划分区别于行政区内其他地区。经济特区边界内的税收、外汇、土地、金融、贸易等方面实行一系列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制度安排,同时实施特定的管理架构和职权。在中国经济处于集聚发展的阶段,经济特区为区域经济吸引投资、促进贸易、引进人才、激发活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2. 产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1979年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设立和1984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挂牌,拉开了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序幕。这些专门功能的产业园区和经开区侧重经济开发建设,主要任务是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形成产业集聚、打造产业生态,目的是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大部分在建立初期都隶属在某一行政区划内,地理范围小于行政区,管理模式以设立管委会为主,被赋予特殊的经济开发管理权,与所在的行政区的经济管理框架高度分离。如蛇口工业区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管委会相当于总公司,各专业公司相当于子公司。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经济区仍由所在辖区的政府统一管理,这一格局通常会引起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利益割裂,形成冲突。

3. 国家级新区。和经开区不同的是,国家级新区同时承担经济开发和城市功能开发的任务。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是1992年成立的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从沿海到内陆,又陆续批准了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多个新区。国家级新区在创建初期的主要任务基本都是土地成片开发、产业集聚等经济任务,因此借鉴了当时经开区的管理经验,大多也采取封闭的、与所在行政区管理框架高度分离管理模式,即管委会为主导的政企并存模式。例如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于1993年正式成立,下设10个委办局,负责统一规划、成片开发和社会管理等工作。1990年9月成立的陆家嘴、外高桥、金桥3个开发公司分别负责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的开发和运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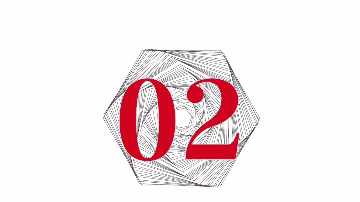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在进一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促进相对平衡的要求下,2003年苏南地区开始尝试实践正向“飞地经济”, 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江苏、浙江、东北及中部地区为主的“飞地经济”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区划限制,以生产要素的互补和高效利用为直接目的,在较低水平区域(飞入地)建立经济区,并在经济区内引入行政区级别较高(飞出地)的经济发展权限和其他政策,搭建类似“理事会+管委会+开发公司+投融资平台”的管理框架,使得经济区的管理框架不受到所属行政区管理体制的束缚,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在两区高效流动。再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利益分配等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这一阶段飞地经济实践的主要特征是:分责型管理,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较高。同时,经济特区、开发区和国家级新区等开始探索“区政合一”的管理模式,经济区与行政区由从前的高度分离逐步向低度分离转变。
1.飞地园区。江阴-靖江工业园是国内首个跨江、跨行政区域的开发园区,成立于2003年。园区地处靖江市,建立初始的管理体制就是社会管理事务由园区所在的行政区靖江负责,靖江市政府在园区成立办事处,负责社会事务。江阴市政府在园区成立管委会,负责投资开发和运营管理。决策机构是两市共同成立的“联动开发协调委员会”,此外两地还明确了利益分配机制,比如江阴、靖江按照9:1的比例共同出资1亿元用于园区建设;10年内两市不得从园区提取投资收益;10年后若有收益分成,两市各得50%等。此模式是典型的分责型管理,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较高,优点是飞出地江阴可以全面统筹规划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快速导入资金和项目,快速复制推广江阴的经验。缺点是基于行政区靖江的管理权限设置,经济区的经济事务与行政区的社会民生事务难以完全切割,同时经济区与周边地区统筹协同考虑较少。截至2016年,江苏飞地经济合作园区(经济区)共计45个,其中38家是省域内合作,7家是省级合作。之后,跨省合作也逐步兴起,如上海外高桥集团启东产业园、漕河泾海宁工业园等。

2.经济特区、开发区和国家级新区。在这一阶段,早期成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的区域范围也都在2010年左右扩大到全市范围,使得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地理范围完全重合,实现了区政合一,管理框架也完全重合,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制度距离基本消失了。一些开发区、国家级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产业逐渐集聚到一定规模,城市基础设施的功能也逐步完善,开始吸引大量人口流入,并逐步与所在行政区或邻近行政区开始实行“区政合一”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职能整合、机构整合、功能整合,实现优势互补。例如浦东新区在2000年8月建制,正式由管委会体制转为一级政府管理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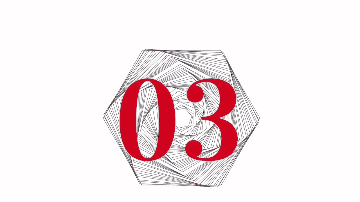


适度分离探索(2016年-至今):
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并重
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通过发展“飞地经济”等方式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和互助机制。2017年6月,《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创新“飞地经济”合作机制,积极探索主体结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新模式,飞地经济逐步进入更加多元化的表现阶段。同时,随着集聚与平衡的持续推进,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跨区域流动,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均等和基础设施共享等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实现格局重构和再次整合,成为实现区域均衡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平衡的路径从之前经济增长极的传导进一步转向经济社会全方位的面上推进。这一阶段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改革探索逐渐进入跨区域联合经济区的打造,主要特点是:要素重构,经济区与行政区逐步转向适度分离。
1.形式多元的飞地经济。2016年开园的衢州海创园是浙江省第一块创新型“反向飞地”。衢州位于浙江省西部,经济总量较小、产业结构偏重、高端人才匮乏,地区发展受到制约,通过在杭州建立“反向飞地”,充分将杭州地处长三角核心科创区块、人才高地、金融服务集聚的资源和要素优势反向赋能衢州,推动了衢州产业转型升级。反向飞地是欠发达地区(飞入地)主动出击,在较高水平区域(飞出地)建立经济区以获得人才、创新等资源,虽然也打破了区划限制,但与正向飞地不同的是,经济区所在的行政区是飞出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区可以享受飞出地的经济发展权限和相关政策,例如入驻衢州海创园的企业员工能够享受杭州市的政策补贴和社保服务,降低了经济区与行政区的管理架构分离程度,缓解了制度摩擦;而另一方面经济区本身也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和发展权限,入驻衢州海创园的企业可以享受租金减免、税收优惠等附加政策,这样的管理架构又适度区别于行政区,更大程度地赋能飞入地。
再比如双向飞地,是正向飞地和反向飞地两种模式的互联,欠发达地区在发达地区设立反向飞地,为产业链提供创新链服务;另一方面,发达地区产业承载空间有限,就在欠发达地区积极布局产业飞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例如2018年以来,浙江温州和上海嘉定区在嘉定共同设立科创园,温州企业可以来嘉定共享科技资源,在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设立实验室、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同时在温州设立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嘉定工业区温州园),嘉定的企业可以在温州拓展生产基地。此种模式下,经济区分别嵌入对方的行政区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地充分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不断强化政策协同,实施营商环境共建以及监督执法联动等,经济区与所处行政区的分离程度始终处于不断优化调整中,最大程度地赋能彼此。

衢州海创园(图源:百度)
2.跨区域联合经济区。指的是在都市圈或者城市群范围内,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发展相融且分属于不同行政区的地区联合设立的经济区,在尊重既定多个平行行政主体管理架构的前提下设立联合经济区协调机构,通过跨域具体项目的实施,发现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后倒逼制度创新,并提出推进一体化推进的共同行为准则,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与模式,如建立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分工协作的区域产业体系、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政策、跨区域合作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等。也就是说各个地区既要尊重自身制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又要遵循这一特殊区域的规则。跨区域联合经济区最早的实践探索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在上海正式挂牌,12月,上海经济区最终划定的范围是上海市和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一市。由于跨多个行政区,这些地区在发展基础、城市能级上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以“上海规划办”作为枢纽性协商性机构,通过编制规划、建立会议机制、搭建横向联合平台等行政协调方式来组织开展经济活动。各地区既要尊重自身制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又需要体现这一特殊区域的规则,只能在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夹缝中进行有限度的探索,管理框架管理边界不明晰,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度较低,总体上对“条块分割”触及不大,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但总体上收效甚微。
2019年11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揭牌成立,范围包括上海青浦、苏州吴江、嘉兴嘉善全域,面积约2413平方公里,涉及多个跨省级平行行政主体。和之前上海经济区不同,示范区在共同管理、协同治理方面不断进行体制机制突破,搭建了“理事会+执委会+发展公司”的三层次管理架构,理事会是协商沟通机构,执委会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示范区新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是开发建设主体,由沪苏浙两省一市等额出资、同股同权,出资主体包括青浦、吴江、嘉善等所属的国有企业。在这样的架构下,一方面协商沟通合作的内容是否畅通取决于三者之间行政区的共同诉求,共同诉求强烈,各行政区就愿意让渡部分权力给协调机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同股同权、共同出资等方式加深了三地的利益捆绑,有利于示范区建设纵深推进。2024年5月,三省市又制定了《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用立法将制度创新上升为法条,体现了刚性约束,同时还出台了相应的授权性规范和支持性、鼓励性条款,为深化改革预留空间。这种管理框架基本没有打破既有行政经济区关系,表面上看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分离程度较低,各行政区之间的矛盾与摩擦较少,行政破壁程度有限,但却通过市场化机制的介入以及立法保障加强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提高了资源配置水平。此模式下,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分离程度被体制机制优化调整至“适度分离”。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图源:百度)
综上,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改革探索是寻求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最佳耦合点”,以解决行政区对经济区发展形成的制约。

参考文献:
1. “制度距离”对区域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及其治理应对 —— 来自全球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与启【J】,张京祥、王雨,国际城市规划 ,2023(5),56-65
2.尺度重构理论视角下经济区与 行政区适度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 * ——基于 20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谢来位、常阳,中国行政管理,2023 (12),61-72
3.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历史阶段、内在本质与政策建议, 【J】, 黄伟 蔡之兵,中国国情国力,2023(1),65-68
4.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视角下 武汉都市圈的协同治理,柳青,2022(12),54-58
5.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早期实践: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经济区概念的提出与演变过程探析,林盼【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5),142-154
6.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院 实践逻辑尧典型模式与取向选择【J】, 蔡之兵、 张可,改革,2021(11),30-41
7. 创新要素的跨域重组:机制、 困境与路径创新【J】,胡航军、张京祥,城市规划学刊,2024(1),74-81
8.论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的管理模式【J】,盛 毅、杜雪锋,开放导报,2020(5),28-33

- E N D -
作者:浦亦稚
编辑:龙彦霖
商务合作丨zhongchuangyanjiu@163.com ,17157425293 简历投递丨zcyj_sh@163.com ,021-58211319 、13301834828
通讯地址丨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4楼B203-B205室
信息系统
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官方公众号
中创云
知识库系统